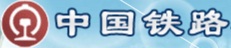不少游客一开始对云南建水的印象只是一座古老的城楼,但如果不亲自到建水古城,就体会不到这里丰厚的历史沉淀。这里的古建筑雄伟奇特,老井遍布全城,精美的民居大院不计其数。每天沉浸在古韵濡染的欢愉之中,为一处又一处寻访到的古迹而由衷赞叹。白天饱餐精神食粮,晚上回来还可以遍尝建水的美食,这又是另一种抵挡不住的诱惑。各式米线、烧烤,美食自选,惊叹那么多新奇菜肴可以烤着吃。又有高雅的汽锅宴,由建水紫陶砂锅喷蒸而成的佳肴,美味绝伦。

碗窑村古“龙窑”
建水的碗窑村在泸江支流绣球河边,只有几十户人家。村前绣球河涓涓流过,村后张家沟后山俨然天然彩屏,蕴藏着丰富的五彩陶土。自1000多年前起,碗窑村的居民就大多以烧制陶瓷为生。
在碗窑村一个四层楼的家庭作坊里,经常可以看到几个工人正忙得热火朝天。这个家庭作坊的主人就是现代紫陶的主要传承人之一的陈绍康老先生。陈绍康一生都是在这些瓶瓶罐罐中度过的。他家三楼的玻璃柜中,展出了许多美轮美奂的紫陶工艺品,或古朴,或淡雅,既有大家笔墨俊逸的气韵,又隐隐听到金石之声。
建水紫陶不叫紫砂陶而叫紫陶,泥料是最本质的区别。泥浆经过滤浆后,经过五六次反复的搅拌漂洗,然后在透气封闭的状态下自然凝干成泥,整个过程要经过20天左右的时间,这时的泥料已腻如膏脂。尔后要经过拉坯,拉坯时“心要正、眼要准、手要稳”,唯有此,才能造就一件正品紫陶作品。
对陶坯落墨后,刻工艺人必须立刻将墨迹雕刻成模。经填泥、修坯、风干、焙烧、分次打磨抛光以后,线条会呈现好似经千年锈蚀风化而斑驳陆离的肌理变化,于是便有了金石之气的天生古拙。紫陶刻工多为女工,她们心细手巧,起落之时游龙走凤。紫陶出名了,大师出名了,她们的名字却从来没有被留在陶瓶上,只是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平凡与单调。残帖的装饰是建水紫陶独具匠心的创造,是所有陶瓷中仅限于建水紫陶独特的语言。
不过,即使是陈绍康家也用上气化窑来烧制紫陶了。现在的碗窑村唯一还在坚持用龙窑的是陈外元夫妇。“龙窑”是人们对烧制紫陶的土窑的称呼,龙窑一般建在坡度30°左右的山坡上,头朝下,尾在上,长可上百米,短亦十数米,形似从天而降的蛟龙。龙窑在建水出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末期。陈外元总是很遗憾地摇摇头说:“都不用了,都不用了,好东西呀。”现在人们通常使用现代化的气化窑,成品率可以在95%以上。而龙窑的成品率通常不会超过七成。但龙窑有它的魅力,当龙窑窑膛温度达到摄氏1200℃时,紫陶呈色就会出现奇异的窑变,或黑或绛或红紫相间,出现可遇而不可求的神奇色彩。窑变后的建水陶,像云彩一样神秘而又捉摸不定。

朱家花园
在建水地方志上,能看到许多举人进士的事迹,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为能臣大儒,他们廉洁清明,尤以直谏不讳为人称颂,这种入世风格大概是受建水人心性单纯、直来直往的影响。据说明清时开科取士,云南一榜举人中临安学士竟占半榜之多。
先师廊下,几个老人在下着象棋,小孩子们拿着树枝从一头跑到另一头。几百年来,建水文庙以其祭祀、教学、礼乐功能,和睦边疆民族,胜过百万雄兵。至今,建水人还经常在文庙举行“拜师礼”、“成童礼”、“成人礼”、“敬老礼”,这里更是新人们举行婚礼的首选地方。
建水的朱家花园,就讲述了在这样的风气下,一个家族辉煌与没落的故事。朱家自朱广福起家,在个旧周边开采锡矿,成为整个红河地区最大的矿老板,并在整个西南地区,乃至两广、香港越南等地共形成50多家商号,积攒下了一份很大的家业。
朱家花园有梅兰竹菊四个厅,很多房间如今都被改成了客房,可供游客住宿,颇受老外亲睐。朱家小姐的闺房如今也挂上纱帐,作为景点之一供游人欣赏拍照,很多游人还会上去躺一躺。
走出客房所在的“菊苑”,转左来到一个天井,回头一看,上书“四水归堂”,寓意天下钱财如雨水般皆进朱家,非常气派。天井左右两侧是两条甬道,分别通向大门和朱氏宗祠。绕过宗祠,我马上被书写于外墙上的“朱子家训”所吸引,“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家门和顺,虽饔飧不济,亦有余欢;国课早完,即囊橐无余,自得至乐。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守分安命,顺时听天。”

团山村的明清宅门
出建水县城西行十多公里,转下乡村公路,看见一条青灰色的古石板路自西向东拾级而上。迎接我们的是一个阁楼式建筑,这就是团山村的东门,屋脊上铺满了灰黑的瓦片,飞檐翘首,像一座古老的庙宇。
团山村现保存完好的汉族传统民居和古建筑有21座,它们都已经被编了门牌号,大多数民居仍然有村民居住着。团山村200余户人家中,竟有100多户还保留着斗飞檐、雕梁画栋的明清式大宅门。这些宅院墙面斑驳,大门的彩漆早已辨不清颜色,似乎当年光鲜地建成后就没再修整过,年岁渐过,再怎么粉刷也不复当年的辉煌,也就随它去了。

老宅
村子最北头有一座如今没有住人,保管得最齐整的大宅院,就是当年规模最大,最显赫的人家居住的“张家花园”。据说明洪武年间,江西鄱阳一位名叫张福的商人把生意做到了这儿,便在团山村安家落户,繁衍子孙,成为一方巨族。张福的到来一定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新的观念,使他们纷纷走出家门,在外为官、经商、开矿,最终修筑了一座座殷实的宅院,构建出一个与世无争的小城池。

即将消失的手工
团山村其他的大户人家的宅院都在新中国建立初期被分给村民了,几家合住一院-,各自垒墙隔屋,环绕天井的四合楼廊已不能“跑马转角楼”,但大杂院内,“四合五天井”、“三坊一照壁”的建筑特色随处可见。这里大多数人家门口还贴着残破的春联,有的还高挂着蒙了尘的大红灯笼,却不觉得落魄,只感叹村民生活的随意而漫不经心。在人们对古宅一代代的传承中,在炊烟一直未断的民宅中得以如此的保存,实在是活民居中不可多见的奇观。
团山村知雯园中那座法国自鸣钟,永久地定格在了6时10分,正好与我往回走的时间一样。赶上最后一班回建水的小黄车,路边夕拾朝花的妇人挑着两大袋鲜花,赶着水牛缓缓路过。仿佛从哀哀婉婉的江南梦中醒来,你知道这里还是热情淳朴的滇南,那些幽怨哀思在大太阳底下来不及蒸发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