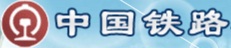一、赞歌
赞歌是从萨满教神歌演化而来,是信仰萨满教的蒙古人从对所崇拜对象的神性赞美到现实的理性赞美发展的结果。如赞美山川四季的赞歌是从祭山祭水祭候鸟的神歌演化而来,是人们从对神山、神水及其与种鸟(候鸟)联系的四季变化的神性赞美到山川四季给予人们的物质利益、精神愉悦的现实理性赞美发展的产物;赞马歌是从和祭敖包联系在一起的男子三项游戏中的赞马词演变而来,是人们从对马的神性赞美到现实的理性赞美发展的结果。
随着神性赞美逐渐淡化隐没、现实理性赞美逐渐强化突出趋势的发展,赞歌所赞颂的对象也就逐渐脱离了萨满教所崇拜的对象,出现了赞颂汗主、大臣、将军、佛教、寺庙、高僧等多方面的内容。在我们第一节提到的经过断代鉴定的两种资料中,赞颂多方面内容的赞歌数量已经很多。例如《蒙古乐曲》第四十七卷《笳吹乐章》的第17首《明光曲》,即是赞颂汗主的一首赞歌:
要说太空的装饰,
是太阳月亮二者:
要说人间的精华,
是汗主汗后两个。
二、思亲思乡歌
思亲思乡歌的生活基础主要是蒙古族族外婚制的远娶远嫁相对内对外战争中的远征远戍,思想根源则是传统的亲族观念和对父母长辈的孝敬心理。所以从思想内容的发展演变考察,思亲思乡歌和婚礼歌中的送亲歌、和兵役歌、和宣扬孝道的谚 语格言歌都有关系。本书第一卷蒙、元民歌第三节评介的两首兵役歌《金帐桦皮书》和《阿莱钦柏之歌》,实际都具有思亲思乡歌的性质。远嫁思亲思乡歌的产生也应该是比较早的。从断代比较明确可靠的《蒙古乐曲》、《阿鲁杭盖民歌300首》看,都收录有不少这类歌曲。
三、佛教歌
佛教歌是十六世纪末以后黄教在蒙古地区民间普及渗透时期产生的歌类。从《蒙古乐曲》、《阿鲁杭盖民歌300首》两种资料汇集看,其作品数量所占比重较大,这说明,这类歌在当时十分盛行。《蒙古乐曲》有词有曲的歌73首,其中近一半属于佛教歌曲;《阿鲁杭盖民歌300首》,其中近三分之一属于佛教歌曲。而在这近一半和近三分之一的佛教歌曲中,大部分属于喇嘛高僧和文人学士的书面作品。这进一步说明,佛教歌曲盛行的原因,主要是封建上层统治阶级对佛教的支持倡导和寺庙高僧对经教学说的传播灌输,下层群众虽有某种程度的迎合,但从根本上说是被麻痹被毒害者。所以,就思想内容看,高僧文人创作和产生自下层百姓的佛教歌曲具有明显的区别。一般说,产生自民间的歌曲不像高僧文人的创作那样说教周祥、充满经卷气息。一方面,下层百姓只是跟随封建统治阶级对"三宝"、"政教两权"等迷信教条进行盲目的赞颂;另一方面,他们是从自身的利害出发来理解佛教,特别容易接受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一类的说教,他们除希望法力无边的神佛能惩恶扬善,主持公道外,还祈求仁慈的佛爷能保佑自己,消灾祛难。
四、情歌
情歌产生于什么时候,目前还说不清楚。根据搜集到的作品资料,晚清以前开始流行是没有疑问的。1918年成书的《蒙古风俗鉴》记录了一首题名为《昂斯拉》的情歌,作者罗布桑却丹介绍说,这首歌已流传近百年。《阿鲁杭盖民歌300首》中约有情歌30余首,所占比重不是很大,也不是太小,说明当时情歌已比较流行。
昂斯拉是一个美丽的姑娘的名字。传说因昂斯拉生得像蝴蝶一样漂亮,很多男子都日夜思念她,想得到她。《阿鲁杭盖民歌300首》中的情歌则大都表现了男女之间的相互爱慕之情和不能自由恋爱择婚的痛。
长着机灵剪耳的紫骝马,
不知你何时能成为我的坐骑?
真心相爱的姑娘,
不知何时能配得上你?
…………
如果没有漫天的风雷,
我就能够伴随着温暖的阳光;
如果没有严厉的法规,
我就能够娶你到我的毡房。 (《机灵剪耳的紫骝马》)
赛场的跑马再快,
也脱不出手中的缰绳;
幽会的情人再躲,
也躲不过众人的眼睛。
颠跑的快马再狂,
也害怕路途的砾石滚滚;
相爱的恋人再热,
也畏惧众人的议论纷纷。(《黑颠马》)
这说明,早期的蒙古族情歌虽然曲折地流露了青年男女追求自由爱情的愿望,但思想感情还受着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较大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