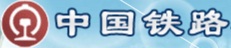辉河发源于大兴安岭中部西北侧的丛山密林中,由二十几条小河汇集于乌拉吉呼,折向西北缓缓流入呼伦贝尔草原,把大草原分为两部分。其左侧被称为巴尔虎草原,右侧则是鄂温克草原。辉河河道开阔平坦,河水弯弯曲曲流至宝力格东又折向东北,汇入伊敏河。辉河水坝距河口14公里,属于鄂温克族自治旗锡尼河西苏木(乡)境内。北距海拉尔市33公里。
一、遗址
辉河水坝长1 200米,把河右岸的毛希浑道布和左岸的特默呼珠山连接起来,该遗址分布在毛希浑道布台地上。早在60年代修水坝取土时,遗物大量暴露出来。水坝南则(上游)形成一个约4平方公里的湖面,左岸河谷形成大片低洼草塘,毛希浑道布成为洼中台地。遗址即在从水坝东端起、沿河崖向北延伸500米,宽约40米的河崖上。
二、地层
试掘地点选在辉河水坝北侧320米处,靠河崖开1×2米探方一个,共出土遗物314件。这里的土质单一,均为细沙土壤。只能依靠出土遗物大致区分为六层。第一层,深18厘米,为地表土层,不见遗物。第二层,深18~30厘米,土质为黑褐色细沙,含有炭粒和油迹。出土细石器、石片等27件,骨片8件,铁片1件。第三层,深30~55厘米,土质与二层无明显变化,仍为黑褐色细沙土。出土遗物丰富,多达174件。其中细石器、石片、石核及石叶共122件,陶片23件,碎骨器残片28件,铁器残片1件。第四层,深55~90厘米,土质由黑褐色渐变为黄色,仍为细沙土。发掘面积缩小为1×1米,出土遗物因此减少到80件。其中细石器41件,陶片13件,骨贝残片3件。从陶片的纹饰、陶质、工艺等分析,文化内涵明显不同于第三层,但地层无明显界线。第五层,深90~110厘米,为黄沙土,出土细石器12件,碎骨(鱼贝类)残片12块。第六层,深110厘米以下,为原生土层,土质为纯净黄色细沙,不见遗物。
三、遗物
细石器共202件,占出土遗物总量的70%。其中石叶55件,石刃25件,石核2件,刮削器21件。其余都是不成形的石片、石料,上有打制、压剥加工的痕迹,有的刃部、尖部很锋利,有刮削、切割使用痕迹,但无法确定其器物名称。
陶片,从距地表30~90厘米地层中,共出土陶片36件,因都很小,无法辨认器形,仅能从陶质、纹饰和生产工艺上大致区分为三类。
Ⅰ类,灰褐陶:多素面,也有篦齿纹饰,泥质,轮制,火候较高。出自深30~55厘米地层中。
Ⅱ类,褐陶:内壁黑色,素面。夹砂,手制,火候较高。外壁多有烟熏痕迹。
灰褐陶:泥质抹光无纹饰,内壁黑色火候较低。有炭黑痕迹。这类陶片均出自45~55厘米地层中,与拉布大林鲜卑墓群出土的陶器相似。
Ⅲ类,有纹饰红褐陶:夹砂,手制,火候较高。其纹饰可分为:细绳纹,线条细且断断续续似虚线。组合纹有呈“之”字形,有呈网络状,均出自深60~70厘米的地层中。
红褐篮纹陶:夹砂,手制,断面呈夹层状,似层层贴制。也出自深50厘米的地层中。
黑褐折划纹陶:夹砂,器形较大,似筒形罐,直口无唇,划纹成网格状,出自深65厘米的地层中。
粗篮纹陶:红褐色或灰褐色,内壁呈黑色,泥质,手制,出自深75~90厘米的地层中。
骨器,均残碎,无法辨认器形的部位,少数碎骨片上有加工使用痕迹。
四、小结
辉河水坝石器遗址尚未正式发掘过,有待确认其考古学文化。从这次试掘出土的遗物分析,这一遗址时代跨度很大。早自无陶的中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铁器时代,都有人类活动的遗迹。
在呼伦贝尔草原上,已发现数百处细石器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精致石镞、刀刃、石核、石叶等。各类细石器的演变序列,虽一时还难以分辨,但在辉河水坝遗址,各种各样的细石器俯拾皆是。
这是一处难得的细石器文化遗址,从这次试掘的1~2平方米探方出土的陶片来看,呼伦贝尔草原上的细石器大体可以划分为四期。
第一期,为中石器时代,即深90~110厘米地层。仅见细石器和鱼类、贝类骨骼化石,不见陶片。
第二期,为新石器时代,即深55~90厘米地层。出土的陶片种类繁多,纹饰有篮纹、绳纹、划纹,在土崖剖面同层位中,还采集到不多见的压印凸网格纹等陶片。显然,在新石器时代,这里繁衍生息了一个又一个狩猎、游牧部落和民族。
第三期,进入历史时期,在深30~55厘米地层中。呼伦贝尔是东胡、鲜卑、室韦等民族的活动范围。出土的陶片与扎赉诺尔、拉布大林、西乌珠尔等古墓群的陶器相似。
第四期,为辽、金、元时期,在深18~30厘米地层和已被破坏的地表中,可以找到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留下的遗物。
辉河水坝的细石器,从早到晚几千年不间断的现象,给“细石器文化”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细石器的加工过程无法充分地把人的文化意识印在石器上,人们在打制(包括压剥)石器简单的加工生产中只能追求其使用价值,即石料的坚硬,石器的锋利。也就是说,细石器仅能反映人的生活、生产方式。
在以渔猎经济为主,或渐渐地向游牧经济形态过渡的漫长历史进程中,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便形成了以食肉习俗为主的部族和民族,他们使用与其习俗相适应的生产、生活用具。在铁器尚未普及的呼伦贝尔草原,从事着狩猎、游牧经济的各个民族,必然长期以石为器,加工成生产工具――石镞,用以狩猎和防身;在日常生活中,也要有相适应的生活用具――石刃、石叶、刮削器、切割器等,用以切割动物皮、肉、筋、刮削木料等。一直延续到铁器广泛应用,锋利万能的蒙古刀走进猎民、牧民的千家万户,“细石器”才悄然离去。